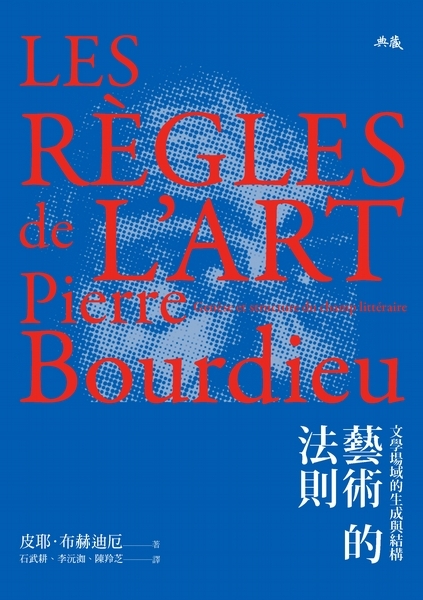眼與心:身體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的最後書寫
NT$250梅洛龐蒂是法國著名哲學家,在現象學運動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闡發了一種獨到的「身體哲學」。《眼與心》原為其生前發表過的一篇長文,最終以單行本形式聞名於世,這是梅洛龐蒂最著名的現象學藝術論。
NT$580
布赫迪厄討論文化生產最重要的作品,為其藝術社會學理論集大成之作!
讓藝術從純粹藝術、美學的探討角度,轉而去分析作家、作品、團體和社會場域之間的關係。
5 件庫存
布赫迪厄討論文化生產最重要的作品,
為其藝術社會學理論集大成之作。
「透過科學分析,對於作品的感性之愛,就能實現在某種對事物的理智之愛。」——布赫迪厄。
皮耶.布赫迪厄(Pierre-Félix Bourdieu, 1930-2002)是法國當代重要的思想家,也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
本書是布赫迪厄以19世紀下半葉的法國文學場域為起點,所展開的一場對於文學與藝術場域的深刻分析。書中,他企圖在場域系統中把社會結構與複雜的情感心理連結起來,並以福樓拜的《情感教育》作為一個寫實主義文本裡的社會生活寫照摹本,深入發揮他的場域理論。
全書共分為〈前言〉、〈序曲〉和三個部分。作者分別在〈前言〉指出當代學術研究問題所在,並提出解決之道;〈序曲〉主要針對《情感教育》的分析;〈第一部〉,以法國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文學與藝術現象,討論了文化生產場域中的自主性問題;〈第二部〉,為藝術作品的系統科學分析設立了基本原理;〈第三部〉,則是對純美學的分析。
布赫迪厄首先提出一個對於文學與藝術作品的質疑,亦即「為什麼那麼多人宣稱藝術作品的體驗是不可言喻?為什麼人們會表現出抗拒文學與藝術作品的科學分析?」對此,他認為社會學家對於文學與藝術作品的科學分析,並不會破壞閱讀或觀賞文學與藝術時的愉悅感受;此種科學分析看似消解了創作者先驗的特殊性,但這全是因為要重建那個圍繞著作者、將作者「像個點一樣地包含進來」的社會權力場域空間,並且在重建工作的最後,再找回這份特殊性。
而福樓拜與其小說《情感教育》即是布赫迪厄實踐此種科學分析的楔子。透過對於《情感教育》當中各個角色的討論,布赫迪厄指出,小說此種文學類型——如同《情感教育》所顯示出的那樣——之所以如此迷人而深具魅力,就在於其呈現了一個「真相」,亦即作者在小說當中所架構出的某種社會世界結構,也即是某種權力場域,在其中,每個角色及其之間,都象徵了在場域當中受到秉性(disposition)與各種慣習(habitus)影響的各個位置(position)、及所佔位者之間的關係。布赫迪厄繼而論證了,無論文學或藝術,所有社會場域的運作,其根源皆是一種「幻象」、一種對於場域內「遊戲」的潛心投入,亦即一種集體生產與複製的集體信仰價值,藉此交織建構出社會世界的意義,同時,也是各個位置之間的認證權力的壟斷與鬥爭。
由此,我們才能夠真正理解在那些由文學作家所打造的幻覺形式(小說),又或者是藝術家所拋出的關於藝術作品的體驗當中,究竟是什麼樣特定的構成條件,使得這些作品得以成立,並受到讀者與觀眾的認可。
本書可謂讓藝術從純粹藝術、美學的探討角度,轉而去分析作家、作品、團體和社會場域之間的關係。
相關文章|文化財擴張:波希米亞派與創造一種生活藝術
➤ 追蹤典藏藝術出版Facebook和Instagram
➤ 尋找更多閱讀靈感 Artco Books Inspiration
作者|皮耶‧布赫迪厄(Pierre-Félix Bourdieu,1930-2002)
法國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曾任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同時也是許多知名著作與社會學期刊的作者與主要策劃者,例如其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即被國際社會學協會評選為20世紀社會學最重要的十部社會學經典之一、他也曾擔任過午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常識」(Le Sens commun)系列的主編、《社會科學的研究行動》(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作者與總編輯等等。
布赫迪厄的理論基礎建立於維根斯坦、梅洛-龐蒂、胡塞爾、康居朗、馬克思、巴舍拉、韋伯、涂爾幹、潘諾夫斯基、牟斯、帕斯卡等哲學家與理論家脈絡之上,論述強調「實踐」與「體現」在社會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會生活中位居宰制與象徵地位之「系統」與「社會秩序」的重要性,由此開創出其著名的「場域」理論。另外,他也反對著沙特所認為的知識分子「先知」或「全能知識分子」之概念,並在晚期轉而發展出「公共知識分子」的意識型態,讓社會學家是否必須將其研究延伸至更大幅度的公共領域成為一重要課題。
譯者|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
導讀
前言
序曲:作為福樓拜分析家的福樓拜
位置、配置、位移
繼承的問題
必然的意外事故
寫作的權力
附錄1:《情感教育》情節概要
附錄2:《情感教育》的四種解讀
附錄3:《情感教育》裡的巴黎
第一部:場域的三態
1. 獲取自主權:場域浮現的關鍵階段
一種結構性的從屬
波希米亞派與創造一種生活藝術
和「資產階級」決裂
奠定律法的波特萊爾
開始喝令遵守秩序
一個有待設定的位置
雙重決裂
一個顛倒的經濟世界
位置與秉性
福樓拜的觀點
福樓拜與「寫實主義」
「把平庸給寫好」
回到《情感教育》
賦予形式
創造「純粹」的美學
美學革命的倫理條件
2. 雙重結構的出現
體裁的特殊性
體裁的差異性和場域的一致性
藝術與金錢
差異性的辯證
特定的革命和外部的變化
知識分子的出現
畫家與作家之間的交流
形式
3. 象徵資產的市場
兩個經濟邏輯
兩種衰退模式
劃時代
變遷邏輯
同源性和預先建立的和諧效應
信念的產生
第二部:一門作品科學的基礎
1. 方法問題
一種新的科學精神
文學信念與抗拒客觀化
「初始設想」,根本的迷思
憤青觀點與偽決裂
觀點的空間
超越非此即彼
將客觀化的主體予以客觀化
附錄:全能知識分子與思想萬能的幻覺
2. 作者的觀點:文化生產場域的幾個普遍特性
權力場域當中的文學場域
律法與界線問題
幻象與受膜拜的藝術品
位置、秉性與佔位
含有種種可能性的空間
結構與變化:內部鬥爭與不斷革命
反思性與「素樸性」
供與求
內在鬥爭與外在制裁
兩個歷史的交會
建構的軌跡
慣習與可能性
位置與秉性的辨證
團體的形成與解散
制度的超越
「小說瀆神的拆解」
附錄:場域效應與保守主義形式
第三部:對理解的理解
1. 純粹審美在歷史中的創生
對於本質的分析與關於絕對的幻覺
歷史溯往與被壓抑事物的回歸
藝術感知的歷史範疇
純粹閱讀的條件
去歷史主義的悲歌
雙重歷史化
2. 目光的社會生成
15世紀之眼
迷人幻覺的基礎
3. 閱讀行為理論
自省小說
閱讀的時間與時間的閱讀
返始:幻覺與幻象
附言:普世性的社團主義
人名索引
概念索引
作者:皮耶.布赫迪厄
出版社:典藏藝術家庭
出版日期:2016.2.25
ISBN:9789869225960
裝訂:平裝
頁數:520
天使:在愛情與文學上特別好用的詞。
——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庸見辭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
在名人蠢語錄裡也不是什麼都有。所以還有希望。
——格諾(Raymond Queneau)
「文學經驗與愛情經驗並列人類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這可是我們生命的意義啊,難道我們就放任社會科學把它化約成對於休閒活動的問卷調查嗎?」從無數年代、無數作者為閱讀與文化做辯護的說辭裡,信手捻來的這種句子,肯定會像那些自命正派的陳腔濫調一樣,引起福樓拜的強烈不滿。還有一些教學生崇拜書本的「陳舊」說辭,或是一些海德格–賀德林(heideggéro- hölderliniennes)式的揭示,每一句的老套程度都值得收入「布瓦爾–貝居榭選集」(florilège Bouvardo –pécuchétien)(格諾的說法……),例如:「閱讀,就是先擺脫自己,再擺脫自己所在的這個世界」;「若無群書之助,在世上也就無處容身」;「在文學之中,本質一下子就顯現出來了,文學是與其真理一起、也在其真理之中呈現的,就好像存在的真理本身,也是自我揭示的一樣?」
我之所以會覺得有必要一開始就提起一些,像這樣談論著藝術與生活、獨特與平常、文學與科學,談論著雖然可以建立法則卻丟失了「經驗的特定性」的(社會)科學,以及不建立法則卻「總是從絕對的特定性來處理特定個人」的文學等等,諸如此類的乏味論點,這是因為這些論點是由學校課程的儀典、也為了學校課程的儀典,而無限地再生產出來的,於是,凡是由學校所陶冶出來的心智,就都將這些論點內建其中了:由於發揮了過濾或屏蔽的作用,因此這些論點總是有可能對人們造成阻礙或混淆,使其難以理解對於書籍與閱讀的科學分析。
在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駁聖伯夫》(Contre Sainte-Beuve)當中,就以典型方式表現過了對於文學之自主性的訴求,而這是不是就意味著,對於文學文本的閱讀,就只能有文學上的意義?學術分析難道真的免不了會摧毀文學作品與閱讀的獨特之處,首先就是審美的愉悅?社會學家就註定要陷入相對主義、追求價值的齊頭平等、貶低偉大之事、撤銷那造就了總是被劃歸獨一無二那邊的「創作者」(créateur)特殊性的種種差異?而這都是因為他就是要跟大多數人、平均值、中等站在一起,所以就要跟平庸、次等、平民(les minores)、還有一大群沒沒無聞也活該不為人知的小牌作家站在一起,要跟當前的「創作者」最痛恨的這些東西,如內容與脈絡、「參照」(référent)與文本之外的事物、還有文學之外的事物站在一起?
許多長年閱讀文學的作家與讀者,更不用提還有好些層次不一的哲學家,包括柏格森(Henri Bergson)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但不止於此,他們都想為科學設下一些先驗的界限,這對於他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這裡還不計有些人根本就禁止他人用社會學去對藝術品做任何褻瀆式的接觸。這時或許還可以引述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因為他把某種不可理解性、或者至少是不可解釋性的基本假定,當成他那「理解之藝術」的出發點:「藝術品代表了對我們理解力的一項挑戰,因為藝術品無限地逃脫一切解釋,對於想將藝術品解說成與概念等同的人,也提出了某種始終難以克服的抵抗,但對我而言,這個事實恰巧是我詮釋理論的出發點?」我並不是要去討論這個基本假定(不過它經得起討論嗎?)。我只是想問,為什麼這麼多的批評家、這麼多的作家、這麼多的哲學家,都能如此自信滿滿地宣稱,對於藝術作品的體驗是不可言喻的,這個體驗從定義上就是不屬於理性認識的;為什麼他們都如此迫不及待地在知識上未戰先降;他們哪來這種這麼強烈的需求,要貶低理性知識,哪來這種狂熱,要斷定藝術品是不可化約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超驗的。
為什麼人們堅持要賦予藝術品——以及它所喚起的認識——這種特殊的地位?難道不是因為有人提出了種種(必然費力又不完善的)企圖,想要用普通科學的平凡對待方式,來處理人類活動的這些產物,所以就用某種出於偏見的中傷來打擊他們,藉此就肯定了懂得識別其超驗性的那些人(在精神上)的超驗性?為什麼人們要這樣追殺試圖推進關於藝術品與審美體驗之知識的那些人呢?難道不是因為,對這個不可言喻的東西(individuum ineffabile)、以及產製了它的那個不可言喻的個體(individuum ineffabile)進行科學分析,這個抱負本身,就致命地威脅了那種如此普遍、卻又如此「別致」的自負,使人自以為是那不可言喻之個體,並且能夠感受那不可言喻者的各種不可言喻之體驗的自負?簡單說,為什麼人們會表現出這樣一種對於分析的抗拒,難道不是因為,對於「創造者」、以及想要透過「創造式」閱讀來把自己等同於創造者的人來說,這種分析,用佛洛伊德的說法就是,給他們的自戀傾向帶來了最後的、或許也是最深的創傷,一如先前那些以哥白尼、達爾文以及佛洛伊德自己為名的分析所為嗎?
把根本就是戀愛經驗的不可言喻經驗拿來當作藉口,從作品的不可言喻獨特性來把握作品,把對於作品的放縱式的沉醉當成愛情,再把這當成是唯一適合藝術品的認識形式,這難道是正當的作法嗎?這樣就可以把別人對於藝術、以及對藝術之愛所進行的科學分析,看成是科學傲慢的典型表現,認為別人以解釋為藉口,一心威脅「創作者」與讀者的自由與特殊性嗎?對於所有這些堅持無法認識之事、為人類自由築起堅不可摧的城牆以抵禦科學進犯的人,我要以歌德(J. W. Goethe)這段很有康德風格(Kantien),而且所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專家也都會同意的話來反駁:「我們的意見是,人有理由假設某樣東西是不可認識的,但卻不應為自己的探索設下限制。」我想康德就將眾多學者對於他們事業的看法表達得很好,因為他提出,認識與存在的調和,不過是某種想像點,是某種想像中的消失點,科學雖然應該往這個方向努力,卻萬萬不能妄想以此作為根基(他反對的是關於絕對知識以及歷史終結的幻覺,但是這種幻覺在哲學家當中比在科學家當中更普遍……)。至於有人主張科學會給文學經驗的自由與特殊性帶來威脅,若要對此正本清源,則只需觀察到,是科學帶來並提供了這種能力,給所有願意也能夠擁有它的人,使他們不但可以解釋與理解這種經驗,也由此給出了某種可能性,使其可以獲得相對於其種種決定因素的真正自由。
更有正當性的擔憂或許是,對藝術之愛一旦挨上了科學的手術刀,就會把愉悅也一起害死,因為科學雖然可以讓人理解,卻無法讓人感受。於是我們只能附和像是沙尤(Michel Chaillou)所做的一樣的嘗試,以感性、體驗、感受的優先為基礎,提出一種文學生活的文學追憶,雖然在文學性質的文學史當中很奇怪地沒人這樣做過:他想盡辦法,在限定的特殊文學空間之中,重新引進了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所說的「附錄與補遺」(Parerga und Paralipomena),也就是種種被人忽略的文本周遭背景、所有被普通消費者丟開不顧的東西,而他又透過命名的神奇功效,喚回了那造就並組成作者之生活的事物,包括在他們的人生與最日常的場景之中種種放鬆的、家居的、生動的,甚至是怪誕或者「噁爛」的細節,這樣他就對文學興趣的平凡層級進行了某種顛覆。他之所以考據這麼多典故來武裝自己,既不是為了造成對於經典作品的虔誠讚頌,也不是為了鼓勵對於始祖和「亡者遺贈」的崇拜,而是為了召喚讀者,讓他們準備好像聖愛芒(Saint-Amant)所說的一樣「與死者乾杯」:他把被當成神像崇拜的文本與作者從史書與學院派的聖殿裡拉出來,讓他們重獲自由。
要對種種歷史參照進行一種既獲得解放、也使人解放的運用,才有可能建立種種自由的聯想,而這種「歡悅的智慧」就是藉助這些自由聯想,才拋棄了對作者之宏大批評的先知式浮誇,以及教材傳統像僧人念經一樣的碎念,那麼,同樣也必須跟文學聖徒行傳決裂的社會學家,又怎麼會感覺不到自己與這種歡悅智慧的相近?的確,與一般常見的可能令人信服之社會學描述相反,他無法完全滿足於這種對於文學生活的文學式追憶。對於感性的關注,儘管在處理文本時是完全適用的,但若要用來處理產生了這種感性的社會世界,卻反而會讓人忽略掉重點。一個社會學家固然可以努力去使眾多作者與他們的環境復活,也總是有人在進行種種對於藝術與文學的分析,藉以重建某種可以從日常生活的可見處、可感處與具體處去體會的社會「真實」。但是,我在這本書中將會一直試著說明,在這一點上與柏拉圖(Plato)所稱的哲學家相近的社會學家,他與「各色美景美聲之友」,其中也包括了作家,乃是相互對立的:他所追求的這個「真實」雖然是在感性體驗之中顯露的,但此一真實卻不能任人化約成這個感覺經驗的種種立即資料;他所求的並不是讓人看到、或者感覺到,而是要把智識關係的一些體系建構出來,使人得以理解種種感性的資料。
這是否表示,我們又再次落入了老套的理智與感覺的二律背反?事實上,應該要讓讀者來判斷,是不是就像我所認為(而我自己也如此體驗過)的,對於藝術品之生產與接受的種種社會條件進行科學分析,非但不會化約或是摧毀藝術品,反而會強化文學經驗:我們在討論福樓拜時還會看到,科學分析看似率先取消了「創作者」的特殊性,藉以建立有助於理解這種特殊性的種種關係,但這全是為了要重建那圍繞著作者、將作者「像個點一樣地包含進來」的空間,並且在重建工作的最後,再找回這份特殊性。是從文學空間裡的這個點出發,才形成了對於這個空間的特殊觀點,若能如此認識這個點,就能夠透過從心理上去認同某個已然建構起來的位置,藉此去理解與感受,這個位置與佔據這個位置的人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為了使這份特殊性存在,至少在福樓拜的個案裡不可或缺的,這種非比尋常的努力。
對藝術之愛,就像愛情、甚至也尤其是最瘋狂的愛情一樣,都讓人覺得他所愛上的對象就是這份愛的根源。為了說服自己,這樣去愛是合理的(或是有理由的),他就會時常藉助於評論,這種信徒自己向自己辯解的話語,除了至少有強化其信仰的作用之外,還能夠啟發並召喚別人也投入這份信仰。這就是為什麼,當科學分析有辦法指出,是什麼讓藝術品成為必然,也就是其表達公式、生成原理、存在理由,這時科學分析也就為藝術經驗以及隨之而來的愉悅,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證、以及最豐富的養料。透過科學分析,對於作品的感性之愛,就能實現在某種對事物的理智之愛當中,也就是實現在主體對於客體的同化、主體在客體之中的投入,以及對於文學客體之特殊必然性的主動服從當中(而在許多案例中,文學客體本身就是某種類似服從的產物)。
但是,為了像這樣強化經驗,就必須把某樣原本想要被經歷成某種絕對經驗、也跟某項起源之種種偶然無關的東西,化約成歷史的必然性,這樣付出的代價難道不會太高了嗎?實際上,理解文學場域(champ)的社會生成、理解支持這個場域的信仰、理解在場域中進行的語言遊戲、理解在場域中滋生的各種物質性與象徵性的利益與競逐標的,這樣做並不是為了遷就化約或破壞的樂趣(縱使就像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倫理學講義》(Leçons sur l’éthique)裡說過的,在為求理解所做的努力當中,總是有些部分來自於,那些「諸如『這個不過就是那個』之類的解釋」所引起的「摧毀偏見的愉悅」以及「無法抗拒的誘惑」,而在破除藝術崇拜的種種裝模作樣自鳴得意之時尤其如此)。這不過是在面對面觀察事物,並且看出事物的真面目而已。
無論文學場域或藝術場域,都是充滿弔詭的世界,都可以引發或者施加種種最「無關利害」的利害關係,而從這些場域裡,尋找藝術品藏在其歷史性與超歷史性之中的存在原理,這就是將藝術品當作是受到某些其他事物糾纏與調節的、某種具有意向性的符號,因而藝術品也就成了這些事物的徵候。這也就是預設了,有某種表達衝動在此會顯現出來,只是場域的社會必然性所施加的形式化,又會傾向於使這種表達衝動變得難以辨認而已。放棄對於純粹形式之興趣的天真無瑕看法,就是理解這些社會世界的邏輯所要付出的代價,而這些社會世界乃是透過那些,就像社會性的煉金術一樣的,這些社會世界在歷史上的種種運作法則,才終於從種種特定激情與利益之間時常冷酷無情的衝突當中,提煉出了普世性的崇高本質;此外,也為人類的事業所能獲致的最高成果,提供了一種更真切、而且因為不那麼超乎常人、所以最終也更讓人放心的觀點。
| 重量 | 850 g |
|---|---|
| 尺寸 | 14.8 × 21 × 5 cm |
作者|皮耶‧布赫迪厄(Pierre-Félix Bourdieu,1930-2002)
法國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之一。曾任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同時也是許多知名著作與社會學期刊的作者與主要策劃者,例如其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即被國際社會學協會評選為20世紀社會學最重要的十部社會學經典之一、他也曾擔任過午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常識」(Le Sens commun)系列的主編、《社會科學的研究行動》(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作者與總編輯等等。
布赫迪厄的理論基礎建立於維根斯坦、梅洛-龐蒂、胡塞爾、康居朗、馬克思、巴舍拉、韋伯、涂爾幹、潘諾夫斯基、牟斯、帕斯卡等哲學家與理論家脈絡之上,論述強調「實踐」與「體現」在社會建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會生活中位居宰制與象徵地位之「系統」與「社會秩序」的重要性,由此開創出其著名的「場域」理論。另外,他也反對著沙特所認為的知識分子「先知」或「全能知識分子」之概念,並在晚期轉而發展出「公共知識分子」的意識型態,讓社會學家是否必須將其研究延伸至更大幅度的公共領域成為一重要課題。
譯者|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
導讀
前言
序曲:作為福樓拜分析家的福樓拜
位置、配置、位移
繼承的問題
必然的意外事故
寫作的權力
附錄1:《情感教育》情節概要
附錄2:《情感教育》的四種解讀
附錄3:《情感教育》裡的巴黎
第一部:場域的三態
1. 獲取自主權:場域浮現的關鍵階段
一種結構性的從屬
波希米亞派與創造一種生活藝術
和「資產階級」決裂
奠定律法的波特萊爾
開始喝令遵守秩序
一個有待設定的位置
雙重決裂
一個顛倒的經濟世界
位置與秉性
福樓拜的觀點
福樓拜與「寫實主義」
「把平庸給寫好」
回到《情感教育》
賦予形式
創造「純粹」的美學
美學革命的倫理條件
2. 雙重結構的出現
體裁的特殊性
體裁的差異性和場域的一致性
藝術與金錢
差異性的辯證
特定的革命和外部的變化
知識分子的出現
畫家與作家之間的交流
形式
3. 象徵資產的市場
兩個經濟邏輯
兩種衰退模式
劃時代
變遷邏輯
同源性和預先建立的和諧效應
信念的產生
第二部:一門作品科學的基礎
1. 方法問題
一種新的科學精神
文學信念與抗拒客觀化
「初始設想」,根本的迷思
憤青觀點與偽決裂
觀點的空間
超越非此即彼
將客觀化的主體予以客觀化
附錄:全能知識分子與思想萬能的幻覺
2. 作者的觀點:文化生產場域的幾個普遍特性
權力場域當中的文學場域
律法與界線問題
幻象與受膜拜的藝術品
位置、秉性與佔位
含有種種可能性的空間
結構與變化:內部鬥爭與不斷革命
反思性與「素樸性」
供與求
內在鬥爭與外在制裁
兩個歷史的交會
建構的軌跡
慣習與可能性
位置與秉性的辨證
團體的形成與解散
制度的超越
「小說瀆神的拆解」
附錄:場域效應與保守主義形式
第三部:對理解的理解
1. 純粹審美在歷史中的創生
對於本質的分析與關於絕對的幻覺
歷史溯往與被壓抑事物的回歸
藝術感知的歷史範疇
純粹閱讀的條件
去歷史主義的悲歌
雙重歷史化
2. 目光的社會生成
15世紀之眼
迷人幻覺的基礎
3. 閱讀行為理論
自省小說
閱讀的時間與時間的閱讀
返始:幻覺與幻象
附言:普世性的社團主義
人名索引
概念索引
作者:皮耶.布赫迪厄
出版社:典藏藝術家庭
出版日期:2016.2.25
ISBN:9789869225960
裝訂:平裝
頁數:520
天使:在愛情與文學上特別好用的詞。
——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庸見辭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
在名人蠢語錄裡也不是什麼都有。所以還有希望。
——格諾(Raymond Queneau)
「文學經驗與愛情經驗並列人類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這可是我們生命的意義啊,難道我們就放任社會科學把它化約成對於休閒活動的問卷調查嗎?」從無數年代、無數作者為閱讀與文化做辯護的說辭裡,信手捻來的這種句子,肯定會像那些自命正派的陳腔濫調一樣,引起福樓拜的強烈不滿。還有一些教學生崇拜書本的「陳舊」說辭,或是一些海德格–賀德林(heideggéro- hölderliniennes)式的揭示,每一句的老套程度都值得收入「布瓦爾–貝居榭選集」(florilège Bouvardo –pécuchétien)(格諾的說法……),例如:「閱讀,就是先擺脫自己,再擺脫自己所在的這個世界」;「若無群書之助,在世上也就無處容身」;「在文學之中,本質一下子就顯現出來了,文學是與其真理一起、也在其真理之中呈現的,就好像存在的真理本身,也是自我揭示的一樣?」
我之所以會覺得有必要一開始就提起一些,像這樣談論著藝術與生活、獨特與平常、文學與科學,談論著雖然可以建立法則卻丟失了「經驗的特定性」的(社會)科學,以及不建立法則卻「總是從絕對的特定性來處理特定個人」的文學等等,諸如此類的乏味論點,這是因為這些論點是由學校課程的儀典、也為了學校課程的儀典,而無限地再生產出來的,於是,凡是由學校所陶冶出來的心智,就都將這些論點內建其中了:由於發揮了過濾或屏蔽的作用,因此這些論點總是有可能對人們造成阻礙或混淆,使其難以理解對於書籍與閱讀的科學分析。
在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駁聖伯夫》(Contre Sainte-Beuve)當中,就以典型方式表現過了對於文學之自主性的訴求,而這是不是就意味著,對於文學文本的閱讀,就只能有文學上的意義?學術分析難道真的免不了會摧毀文學作品與閱讀的獨特之處,首先就是審美的愉悅?社會學家就註定要陷入相對主義、追求價值的齊頭平等、貶低偉大之事、撤銷那造就了總是被劃歸獨一無二那邊的「創作者」(créateur)特殊性的種種差異?而這都是因為他就是要跟大多數人、平均值、中等站在一起,所以就要跟平庸、次等、平民(les minores)、還有一大群沒沒無聞也活該不為人知的小牌作家站在一起,要跟當前的「創作者」最痛恨的這些東西,如內容與脈絡、「參照」(référent)與文本之外的事物、還有文學之外的事物站在一起?
許多長年閱讀文學的作家與讀者,更不用提還有好些層次不一的哲學家,包括柏格森(Henri Bergson)與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但不止於此,他們都想為科學設下一些先驗的界限,這對於他們來說是理所當然的。這裡還不計有些人根本就禁止他人用社會學去對藝術品做任何褻瀆式的接觸。這時或許還可以引述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因為他把某種不可理解性、或者至少是不可解釋性的基本假定,當成他那「理解之藝術」的出發點:「藝術品代表了對我們理解力的一項挑戰,因為藝術品無限地逃脫一切解釋,對於想將藝術品解說成與概念等同的人,也提出了某種始終難以克服的抵抗,但對我而言,這個事實恰巧是我詮釋理論的出發點?」我並不是要去討論這個基本假定(不過它經得起討論嗎?)。我只是想問,為什麼這麼多的批評家、這麼多的作家、這麼多的哲學家,都能如此自信滿滿地宣稱,對於藝術作品的體驗是不可言喻的,這個體驗從定義上就是不屬於理性認識的;為什麼他們都如此迫不及待地在知識上未戰先降;他們哪來這種這麼強烈的需求,要貶低理性知識,哪來這種狂熱,要斷定藝術品是不可化約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超驗的。
為什麼人們堅持要賦予藝術品——以及它所喚起的認識——這種特殊的地位?難道不是因為有人提出了種種(必然費力又不完善的)企圖,想要用普通科學的平凡對待方式,來處理人類活動的這些產物,所以就用某種出於偏見的中傷來打擊他們,藉此就肯定了懂得識別其超驗性的那些人(在精神上)的超驗性?為什麼人們要這樣追殺試圖推進關於藝術品與審美體驗之知識的那些人呢?難道不是因為,對這個不可言喻的東西(individuum ineffabile)、以及產製了它的那個不可言喻的個體(individuum ineffabile)進行科學分析,這個抱負本身,就致命地威脅了那種如此普遍、卻又如此「別致」的自負,使人自以為是那不可言喻之個體,並且能夠感受那不可言喻者的各種不可言喻之體驗的自負?簡單說,為什麼人們會表現出這樣一種對於分析的抗拒,難道不是因為,對於「創造者」、以及想要透過「創造式」閱讀來把自己等同於創造者的人來說,這種分析,用佛洛伊德的說法就是,給他們的自戀傾向帶來了最後的、或許也是最深的創傷,一如先前那些以哥白尼、達爾文以及佛洛伊德自己為名的分析所為嗎?
把根本就是戀愛經驗的不可言喻經驗拿來當作藉口,從作品的不可言喻獨特性來把握作品,把對於作品的放縱式的沉醉當成愛情,再把這當成是唯一適合藝術品的認識形式,這難道是正當的作法嗎?這樣就可以把別人對於藝術、以及對藝術之愛所進行的科學分析,看成是科學傲慢的典型表現,認為別人以解釋為藉口,一心威脅「創作者」與讀者的自由與特殊性嗎?對於所有這些堅持無法認識之事、為人類自由築起堅不可摧的城牆以抵禦科學進犯的人,我要以歌德(J. W. Goethe)這段很有康德風格(Kantien),而且所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專家也都會同意的話來反駁:「我們的意見是,人有理由假設某樣東西是不可認識的,但卻不應為自己的探索設下限制。」我想康德就將眾多學者對於他們事業的看法表達得很好,因為他提出,認識與存在的調和,不過是某種想像點,是某種想像中的消失點,科學雖然應該往這個方向努力,卻萬萬不能妄想以此作為根基(他反對的是關於絕對知識以及歷史終結的幻覺,但是這種幻覺在哲學家當中比在科學家當中更普遍……)。至於有人主張科學會給文學經驗的自由與特殊性帶來威脅,若要對此正本清源,則只需觀察到,是科學帶來並提供了這種能力,給所有願意也能夠擁有它的人,使他們不但可以解釋與理解這種經驗,也由此給出了某種可能性,使其可以獲得相對於其種種決定因素的真正自由。
更有正當性的擔憂或許是,對藝術之愛一旦挨上了科學的手術刀,就會把愉悅也一起害死,因為科學雖然可以讓人理解,卻無法讓人感受。於是我們只能附和像是沙尤(Michel Chaillou)所做的一樣的嘗試,以感性、體驗、感受的優先為基礎,提出一種文學生活的文學追憶,雖然在文學性質的文學史當中很奇怪地沒人這樣做過:他想盡辦法,在限定的特殊文學空間之中,重新引進了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所說的「附錄與補遺」(Parerga und Paralipomena),也就是種種被人忽略的文本周遭背景、所有被普通消費者丟開不顧的東西,而他又透過命名的神奇功效,喚回了那造就並組成作者之生活的事物,包括在他們的人生與最日常的場景之中種種放鬆的、家居的、生動的,甚至是怪誕或者「噁爛」的細節,這樣他就對文學興趣的平凡層級進行了某種顛覆。他之所以考據這麼多典故來武裝自己,既不是為了造成對於經典作品的虔誠讚頌,也不是為了鼓勵對於始祖和「亡者遺贈」的崇拜,而是為了召喚讀者,讓他們準備好像聖愛芒(Saint-Amant)所說的一樣「與死者乾杯」:他把被當成神像崇拜的文本與作者從史書與學院派的聖殿裡拉出來,讓他們重獲自由。
要對種種歷史參照進行一種既獲得解放、也使人解放的運用,才有可能建立種種自由的聯想,而這種「歡悅的智慧」就是藉助這些自由聯想,才拋棄了對作者之宏大批評的先知式浮誇,以及教材傳統像僧人念經一樣的碎念,那麼,同樣也必須跟文學聖徒行傳決裂的社會學家,又怎麼會感覺不到自己與這種歡悅智慧的相近?的確,與一般常見的可能令人信服之社會學描述相反,他無法完全滿足於這種對於文學生活的文學式追憶。對於感性的關注,儘管在處理文本時是完全適用的,但若要用來處理產生了這種感性的社會世界,卻反而會讓人忽略掉重點。一個社會學家固然可以努力去使眾多作者與他們的環境復活,也總是有人在進行種種對於藝術與文學的分析,藉以重建某種可以從日常生活的可見處、可感處與具體處去體會的社會「真實」。但是,我在這本書中將會一直試著說明,在這一點上與柏拉圖(Plato)所稱的哲學家相近的社會學家,他與「各色美景美聲之友」,其中也包括了作家,乃是相互對立的:他所追求的這個「真實」雖然是在感性體驗之中顯露的,但此一真實卻不能任人化約成這個感覺經驗的種種立即資料;他所求的並不是讓人看到、或者感覺到,而是要把智識關係的一些體系建構出來,使人得以理解種種感性的資料。
這是否表示,我們又再次落入了老套的理智與感覺的二律背反?事實上,應該要讓讀者來判斷,是不是就像我所認為(而我自己也如此體驗過)的,對於藝術品之生產與接受的種種社會條件進行科學分析,非但不會化約或是摧毀藝術品,反而會強化文學經驗:我們在討論福樓拜時還會看到,科學分析看似率先取消了「創作者」的特殊性,藉以建立有助於理解這種特殊性的種種關係,但這全是為了要重建那圍繞著作者、將作者「像個點一樣地包含進來」的空間,並且在重建工作的最後,再找回這份特殊性。是從文學空間裡的這個點出發,才形成了對於這個空間的特殊觀點,若能如此認識這個點,就能夠透過從心理上去認同某個已然建構起來的位置,藉此去理解與感受,這個位置與佔據這個位置的人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為了使這份特殊性存在,至少在福樓拜的個案裡不可或缺的,這種非比尋常的努力。
對藝術之愛,就像愛情、甚至也尤其是最瘋狂的愛情一樣,都讓人覺得他所愛上的對象就是這份愛的根源。為了說服自己,這樣去愛是合理的(或是有理由的),他就會時常藉助於評論,這種信徒自己向自己辯解的話語,除了至少有強化其信仰的作用之外,還能夠啟發並召喚別人也投入這份信仰。這就是為什麼,當科學分析有辦法指出,是什麼讓藝術品成為必然,也就是其表達公式、生成原理、存在理由,這時科學分析也就為藝術經驗以及隨之而來的愉悅,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證、以及最豐富的養料。透過科學分析,對於作品的感性之愛,就能實現在某種對事物的理智之愛當中,也就是實現在主體對於客體的同化、主體在客體之中的投入,以及對於文學客體之特殊必然性的主動服從當中(而在許多案例中,文學客體本身就是某種類似服從的產物)。
但是,為了像這樣強化經驗,就必須把某樣原本想要被經歷成某種絕對經驗、也跟某項起源之種種偶然無關的東西,化約成歷史的必然性,這樣付出的代價難道不會太高了嗎?實際上,理解文學場域(champ)的社會生成、理解支持這個場域的信仰、理解在場域中進行的語言遊戲、理解在場域中滋生的各種物質性與象徵性的利益與競逐標的,這樣做並不是為了遷就化約或破壞的樂趣(縱使就像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倫理學講義》(Leçons sur l’éthique)裡說過的,在為求理解所做的努力當中,總是有些部分來自於,那些「諸如『這個不過就是那個』之類的解釋」所引起的「摧毀偏見的愉悅」以及「無法抗拒的誘惑」,而在破除藝術崇拜的種種裝模作樣自鳴得意之時尤其如此)。這不過是在面對面觀察事物,並且看出事物的真面目而已。
無論文學場域或藝術場域,都是充滿弔詭的世界,都可以引發或者施加種種最「無關利害」的利害關係,而從這些場域裡,尋找藝術品藏在其歷史性與超歷史性之中的存在原理,這就是將藝術品當作是受到某些其他事物糾纏與調節的、某種具有意向性的符號,因而藝術品也就成了這些事物的徵候。這也就是預設了,有某種表達衝動在此會顯現出來,只是場域的社會必然性所施加的形式化,又會傾向於使這種表達衝動變得難以辨認而已。放棄對於純粹形式之興趣的天真無瑕看法,就是理解這些社會世界的邏輯所要付出的代價,而這些社會世界乃是透過那些,就像社會性的煉金術一樣的,這些社會世界在歷史上的種種運作法則,才終於從種種特定激情與利益之間時常冷酷無情的衝突當中,提煉出了普世性的崇高本質;此外,也為人類的事業所能獲致的最高成果,提供了一種更真切、而且因為不那麼超乎常人、所以最終也更讓人放心的觀點。
梅洛龐蒂是法國著名哲學家,在現象學運動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闡發了一種獨到的「身體哲學」。《眼與心》原為其生前發表過的一篇長文,最終以單行本形式聞名於世,這是梅洛龐蒂最著名的現象學藝術論。
面對人類世時代,藝術能做什麼?又做了什麼?
生態紊亂正在加劇,並且嚴重威脅包括人類在內的物種生存。許多藝術創作者意識到「綠色」回應的緊迫性,因而投入(社會)參與、創立生態本質的表達新規範。
臺灣第一女建築師修澤蘭──超越時代的建築先驅者
修澤蘭是臺灣戰後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作品具高度表現性與雕塑性。設計作品類型多元,包括學校、教堂、火車站等,最膾炙人口的代表作為陽明山中山樓、花園新城與衛道中學聖堂。
從日常到創作,漢寶德漫談鄉土與藝術。
本書共分四大卷,從「鄉土藝術家」、「鄉土藝術」、「鄉土建築」,到「老街」,各卷又有名詞義釋與時事探討的詳正論述,諸如鄉土與民間,本土與外來,手工藝與古董等等,倆倆參照又類比影響的相似卻又不一樣,通通都在漢寶德根深淺出的說明比喻裡,談出另一種或更多的可能。
趙無極連年制霸、蘇軾《木石圖》躍居古書畫龍頭、乾隆御製琺瑯彩碗竄升億元關……,回顧2018年拍賣,熱潮雖較往年稍降,整體表現依然亮眼,「拍賣大典」一舉囊括重點拍品,幫助藏家輕鬆掌握下一波趨勢脈絡。
《2015文物拍賣大典》是當今拍賣市場上,資料最豐富的工具書。本書收錄港台、大陸、歐美各大拍賣公司2014年春秋兩季的拍賣精品,分門別類為讀者完整呈現八大類五千多筆拍品精美圖文紀錄。
歐洲/美洲/亞洲等超過100個藝術展覽案例,全面了解當代藝術生產線的生成與脈絡!
這是一本有關當代藝術生產的生態動畫書,也是藝術社會學與人類社會學的移動式視覺對話。
聚焦現當代藝術市場新浪潮!
2017年現當代經典拍品實錄、華人亞洲區排行完整呈現!
【華人】趙無極《29.01.64》2億港幣刷新個人拍賣紀錄
【日本】草間彌生持續引領國際風潮
【韓國】金煥基制霸韓國拍場
【其他】印度、東南亞新生代穩定聚焦
綜觀市場消長,掌握投資風向!藏家必備的最佳拍賣市場指南!
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事,甘願為它克服困難,同時提醒自己:莫忘初心。
還記得熱愛畫畫的心情嗎?
VOGUE、日本觀光局、義美、台北捷運、SOGO合作插畫家 kowei
15年接案歷程分享,獻給所有在藝術這條道路上勇敢、堅持、努力前行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