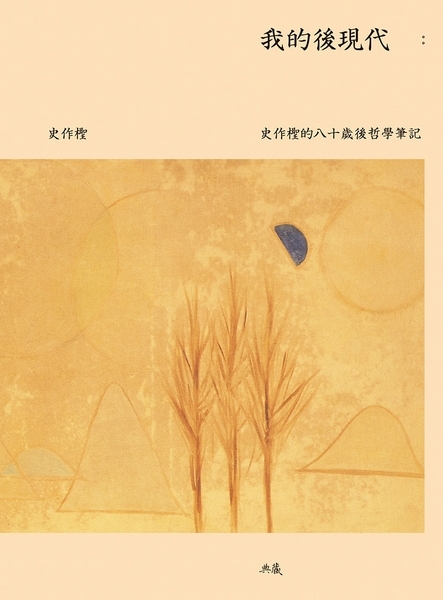哲學方法性基礎之意象邏輯:史作檉的八十歲後哲學筆記
NT$320「意象邏輯」是中國象形文字之圖形表達中之精確化之方法論。
由於它的基礎是圖形表達,所以它完全不同於拼音文字之線性邏輯推演,反之,象形文字圖形表達之精確之方法在於「結構」。──史作檉
NT$320
人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神話。
本文中有著人、自然與文明、神話之間的思考、連繫與互為影響之究真,在「形式遞增,存在遞減」的旨要深耕議論以外,也有靈感隨來隨記的短篇與詩。
9 件庫存
人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神話。
「每一個人都是『人』,也都是『人類』,也是『你自己』。是以每一個人也都必有屬於你自身之『神話』,只是你不曾認真地正視它並加以追索罷了。」——史作檉
本書是史作檉先生近年在民間講堂的授課內容筆記,在企劃擇取後整理成書,較之以往的哲學精神溯源等史論式探討議題,本書共分兩卷,文中有著人、自然與文明、神話之間的思考、連繫與互為影響之究真,在「形式遞增,存在遞減」的旨要深耕議論以外,也有靈感隨來隨記的短篇與詩。
封面與卷頭頁所使用之圖樣皆為史氏親繪畫作,繪畫之於書寫,亦為史氏另一條追索釐辨與抒發自證之方。
作者|史作檉
著名哲學思想家。1934年生,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畢業。擅長以全史觀的視野從哲學、心理學、藝術等層面思考現實的人生信仰、生命現象、文化理念等諸多與人的存在相關的課題,並兼及詩歌創作和繪畫。曾任教於台灣大學、文化大學,並在各地巡迴演講,現以舉辦長期講座為主,深受各方好評。著作等身,影響深廣。
卷一
老人日記
人與文明
生活與知識
續生活與知識
自然與人
聲音
時間與回憶
天上一抹雲
愛、我與大地
卷二
「人」的文明及其未來(一)
「人」的文明及其未來(二)
「人」的文明及其未來(三)
「人」的文明及其未來(四)
「人」的文明及其未來(五)
「人」的文明及其未來(六)
自然與詩的隨想(一)
自然與詩的隨想(二)
自然與詩的隨想(三)
作者:史作檉
出版社:典藏藝術家庭
出版日期:2018.5.10
ISBN:9789869615587
裝訂:平裝
頁數:250
人與文明
1
做為一個人,
我是人,
我是真正的人,
也是實實在在的人,
站在大自然宇宙之洪荒般的世界裡,
我很想設法站到人類文明之邊沿上,審慎地面對整體性的人類文明,看看它到底……
其實,我並不是要刻意地找出人類文明的缺失或病痛,反之:
我在夢中都會夢到,人類文明就是人類發明工具,並在大自然的宇宙中,創意地操作工具,而刻意地創製成一朵屬人之文明之大花,並以此而獻祭在大自然宇宙之上上之神的面前。
可是,以我活了近八十年的歲月來說,這朵由人類所創製之文明的大花,年復一年,它早已殘破不堪,又怎麼再拿來獻祭在大自然宇宙之上上之神的面前?於是有人說,乾脆也叫那上上之神也殘破而毀滅了吧!
儘管如此,可是人本身呢?
就算你可以毀滅一個自然之上上之神,可是你毀得了人要創造真「神」之心嗎?
結果你毀滅了一個上上之神,卻又製造了更多的神,又比原來的真神更差,那到底是誰的錯呢?神的錯嗎?還是文明之錯?而且所謂「神」的存在,只是文明某個角落的事罷了,難道祂真是文明之外,人之上之神嗎?若是,人被夾在中間又將怎麼辦呢?
這事難極了。
這事層層疊疊,疊疊層層,對「人」來說,真是難透了。
所謂上上之神,其實就是自然本身。它不但造就了「人」,同時也使得人造就了「文明」。
如果根本沒有文明可言,那人就自然回到自然本身去了,即如其他一切生物或動物一樣。可是偏偏人會造就文明。如文明有錯,事實上根本就不是文明的錯,而是造就了文明之「人」的錯。若自然造就了人,文明的錯是否也就是自然的錯?其實,這只不過是人在「文明」中這樣想罷了,與自然何關!
自然只是那個真正時間性之行動者,它承載一切而往前走,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所謂時間,也只是人在文明中這樣想罷了。所以,只要人不在文明中,這些問題也就統統不見了蹤影。
一切只有自然多好。其實這就是老子之真義。
可是,我們令老子失望了,因為人偏偏於自然之外製造了文明,而「神」的存在就是人所創製文明中之一大代表。
其實所謂「神」,只是自然的代名詞。你說,神創造人,和自然使「人」的存在成為可能,根本是同一件事。只是當我們說「神」,它確實是一種屬人的文明,而「自然」則很難說。因為在文明中,「神」是需要被再解釋的,如儀式與教義即是。但「自然」就是自然,它似乎不需要再被解釋了,其實這就是老子之所以很難按老子之本來的思想被瞭解、被真實地解釋的原因。
當然這也許只是我一個人的想法,但是所謂「人」,不就是那個善於製造想法的動物嗎?於是必然地,我們就必在文明中了。或只要在文明中,人又製造文明,又必在文明中,這確實是一個很難加以分辨清楚,而又不會遭遇弔詭之事。於是,人在文明中遇難了,他不能不被逼迫,設法使自己果能站在文明的邊沿上來看文明,一如我一開始的那種想像。
其實所謂站在文明的邊沿上,它根本的意思就是說,究竟文明是人所造的,所以事實上,「人」本身就比「文明」大一點。這句話看起來也許很普通,也許是人過分自大或誇大之不可思議的想法。不過,事實是說,如果我們沒有能力站在文明邊沿,而一味在文明之內,其結果很可能我早已被文明所淹沒,不能知道以文明所界定的人,而不再能知道原本創製文明或文明以外之人。不過,只要人甘願,那還有什麼不可以之事!若以一創製文明之人來說,所有既有文明顯然已成為真自然中之「人」,或文明之外之人之一種枷鎖。
總之,「人」的存在可以有三種不同的面向:
一種是以「文明」的方式來看人的存在。
一種是以「人」之做為一個「個體」存在之方式來看「人」。
一種是以自然的方式來看人的存在。
但不論是哪一種方式,都必是以「文明」之方式而說出來的,除非我們連思考的方式或「說」的方式都沒有。那樣一來,恐怕連文明本身的存在都不見了。這恐怕也是一件我們做為一個人所不能想像的事,因為只要有人就必有文明,有文明就必呈現為一種方式。
但只要是在文明中,它又是說明人之物,而人本身又必是突創文明之物,這實在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顛倒。我們想想看,做為一個被出生的「人」,我們可以想像或真知「出生」本身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同理,沒有自然,就沒有人的存在。但我們真能以人的方式來真知自然的存在嗎?儘管人確實是一個和自然無分之物。
一個是因人而有的文明,一個是人因之而有之自然,於是人永遠都是介於自然與文明間之中間物。他真可定奪他自身嗎?
人果可定奪他自身的方式就是文明,或創造文明之方式。但文明本身是一種靜態,甚至是一種「死」的東西,它本身並不會動。相反地,假如我們會認為文明是活的、動態的,甚至是一種果可控制一切或「人」之物,那並不是文明本身之特色,反之,而是由於人參與其中而加以操作之結果。
文明確實可以任人擺佈,但一種真正有能力並有意義的擺佈文明,並不是一件輕鬆而容易的事。一般情形下,人總是將文明與人混在一起,看似他在「文明內」而擺佈文明,不過實際上,絕大部分的情形下人都被文明所擺佈了,只是他尚不能自知罷了。甚至就連我現在操作文字,遵從某些規範,講一些不清不楚的道理,也同樣是在某程度被文明擺佈下而進行的。除此之外,如果我們相信或認定某言論,或一理論、規範、制度、社會習俗,甚至是各式各樣的產品,像是牙膏等等,這些都足以使我們任文明擺佈地形成一種生活模式。但無論如何,這些都無以說明,我們果可成為一不再受文明擺佈之真正或處於文明之外之人之可能。
也許當我們說「文明之外」時,也只是一種文明說法,但至少它已可使我們在文明之擺佈的狀況中,多了一種文明之認知。我想這仍是一件重要而好的事。
就此也並非說,只要我們站在文明外面,我們就果然可以成為一個創製文明之自由者了。不是。人站在文明外面,並非人本身就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存在者了。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如此,可是實際上呢?當人不去面對文明時,事實上他就必須面對另一個比文明之人造物更難以面對並有所處理之真「自然」宇宙。
| 重量 | 480 g |
|---|---|
| 尺寸 | 23 × 17 × 2 cm |
作者|史作檉
著名哲學思想家。1934年生,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畢業。擅長以全史觀的視野從哲學、心理學、藝術等層面思考現實的人生信仰、生命現象、文化理念等諸多與人的存在相關的課題,並兼及詩歌創作和繪畫。曾任教於台灣大學、文化大學,並在各地巡迴演講,現以舉辦長期講座為主,深受各方好評。著作等身,影響深廣。
卷一
老人日記
人與文明
生活與知識
續生活與知識
自然與人
聲音
時間與回憶
天上一抹雲
愛、我與大地
卷二
「人」的文明及其未來(一)
「人」的文明及其未來(二)
「人」的文明及其未來(三)
「人」的文明及其未來(四)
「人」的文明及其未來(五)
「人」的文明及其未來(六)
自然與詩的隨想(一)
自然與詩的隨想(二)
自然與詩的隨想(三)
作者:史作檉
出版社:典藏藝術家庭
出版日期:2018.5.10
ISBN:9789869615587
裝訂:平裝
頁數:250
人與文明
1
做為一個人,
我是人,
我是真正的人,
也是實實在在的人,
站在大自然宇宙之洪荒般的世界裡,
我很想設法站到人類文明之邊沿上,審慎地面對整體性的人類文明,看看它到底……
其實,我並不是要刻意地找出人類文明的缺失或病痛,反之:
我在夢中都會夢到,人類文明就是人類發明工具,並在大自然的宇宙中,創意地操作工具,而刻意地創製成一朵屬人之文明之大花,並以此而獻祭在大自然宇宙之上上之神的面前。
可是,以我活了近八十年的歲月來說,這朵由人類所創製之文明的大花,年復一年,它早已殘破不堪,又怎麼再拿來獻祭在大自然宇宙之上上之神的面前?於是有人說,乾脆也叫那上上之神也殘破而毀滅了吧!
儘管如此,可是人本身呢?
就算你可以毀滅一個自然之上上之神,可是你毀得了人要創造真「神」之心嗎?
結果你毀滅了一個上上之神,卻又製造了更多的神,又比原來的真神更差,那到底是誰的錯呢?神的錯嗎?還是文明之錯?而且所謂「神」的存在,只是文明某個角落的事罷了,難道祂真是文明之外,人之上之神嗎?若是,人被夾在中間又將怎麼辦呢?
這事難極了。
這事層層疊疊,疊疊層層,對「人」來說,真是難透了。
所謂上上之神,其實就是自然本身。它不但造就了「人」,同時也使得人造就了「文明」。
如果根本沒有文明可言,那人就自然回到自然本身去了,即如其他一切生物或動物一樣。可是偏偏人會造就文明。如文明有錯,事實上根本就不是文明的錯,而是造就了文明之「人」的錯。若自然造就了人,文明的錯是否也就是自然的錯?其實,這只不過是人在「文明」中這樣想罷了,與自然何關!
自然只是那個真正時間性之行動者,它承載一切而往前走,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所謂時間,也只是人在文明中這樣想罷了。所以,只要人不在文明中,這些問題也就統統不見了蹤影。
一切只有自然多好。其實這就是老子之真義。
可是,我們令老子失望了,因為人偏偏於自然之外製造了文明,而「神」的存在就是人所創製文明中之一大代表。
其實所謂「神」,只是自然的代名詞。你說,神創造人,和自然使「人」的存在成為可能,根本是同一件事。只是當我們說「神」,它確實是一種屬人的文明,而「自然」則很難說。因為在文明中,「神」是需要被再解釋的,如儀式與教義即是。但「自然」就是自然,它似乎不需要再被解釋了,其實這就是老子之所以很難按老子之本來的思想被瞭解、被真實地解釋的原因。
當然這也許只是我一個人的想法,但是所謂「人」,不就是那個善於製造想法的動物嗎?於是必然地,我們就必在文明中了。或只要在文明中,人又製造文明,又必在文明中,這確實是一個很難加以分辨清楚,而又不會遭遇弔詭之事。於是,人在文明中遇難了,他不能不被逼迫,設法使自己果能站在文明的邊沿上來看文明,一如我一開始的那種想像。
其實所謂站在文明的邊沿上,它根本的意思就是說,究竟文明是人所造的,所以事實上,「人」本身就比「文明」大一點。這句話看起來也許很普通,也許是人過分自大或誇大之不可思議的想法。不過,事實是說,如果我們沒有能力站在文明邊沿,而一味在文明之內,其結果很可能我早已被文明所淹沒,不能知道以文明所界定的人,而不再能知道原本創製文明或文明以外之人。不過,只要人甘願,那還有什麼不可以之事!若以一創製文明之人來說,所有既有文明顯然已成為真自然中之「人」,或文明之外之人之一種枷鎖。
總之,「人」的存在可以有三種不同的面向:
一種是以「文明」的方式來看人的存在。
一種是以「人」之做為一個「個體」存在之方式來看「人」。
一種是以自然的方式來看人的存在。
但不論是哪一種方式,都必是以「文明」之方式而說出來的,除非我們連思考的方式或「說」的方式都沒有。那樣一來,恐怕連文明本身的存在都不見了。這恐怕也是一件我們做為一個人所不能想像的事,因為只要有人就必有文明,有文明就必呈現為一種方式。
但只要是在文明中,它又是說明人之物,而人本身又必是突創文明之物,這實在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顛倒。我們想想看,做為一個被出生的「人」,我們可以想像或真知「出生」本身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同理,沒有自然,就沒有人的存在。但我們真能以人的方式來真知自然的存在嗎?儘管人確實是一個和自然無分之物。
一個是因人而有的文明,一個是人因之而有之自然,於是人永遠都是介於自然與文明間之中間物。他真可定奪他自身嗎?
人果可定奪他自身的方式就是文明,或創造文明之方式。但文明本身是一種靜態,甚至是一種「死」的東西,它本身並不會動。相反地,假如我們會認為文明是活的、動態的,甚至是一種果可控制一切或「人」之物,那並不是文明本身之特色,反之,而是由於人參與其中而加以操作之結果。
文明確實可以任人擺佈,但一種真正有能力並有意義的擺佈文明,並不是一件輕鬆而容易的事。一般情形下,人總是將文明與人混在一起,看似他在「文明內」而擺佈文明,不過實際上,絕大部分的情形下人都被文明所擺佈了,只是他尚不能自知罷了。甚至就連我現在操作文字,遵從某些規範,講一些不清不楚的道理,也同樣是在某程度被文明擺佈下而進行的。除此之外,如果我們相信或認定某言論,或一理論、規範、制度、社會習俗,甚至是各式各樣的產品,像是牙膏等等,這些都足以使我們任文明擺佈地形成一種生活模式。但無論如何,這些都無以說明,我們果可成為一不再受文明擺佈之真正或處於文明之外之人之可能。
也許當我們說「文明之外」時,也只是一種文明說法,但至少它已可使我們在文明之擺佈的狀況中,多了一種文明之認知。我想這仍是一件重要而好的事。
就此也並非說,只要我們站在文明外面,我們就果然可以成為一個創製文明之自由者了。不是。人站在文明外面,並非人本身就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存在者了。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如此,可是實際上呢?當人不去面對文明時,事實上他就必須面對另一個比文明之人造物更難以面對並有所處理之真「自然」宇宙。
「意象邏輯」是中國象形文字之圖形表達中之精確化之方法論。
由於它的基礎是圖形表達,所以它完全不同於拼音文字之線性邏輯推演,反之,象形文字圖形表達之精確之方法在於「結構」。──史作檉
歐洲/美洲/亞洲等超過100個藝術展覽案例,全面了解當代藝術生產線的生成與脈絡!
這是一本有關當代藝術生產的生態動畫書,也是藝術社會學與人類社會學的移動式視覺對話。
聚焦現當代藝術市場新浪潮!
2017年現當代經典拍品實錄、華人亞洲區排行完整呈現!
【華人】趙無極《29.01.64》2億港幣刷新個人拍賣紀錄
【日本】草間彌生持續引領國際風潮
【韓國】金煥基制霸韓國拍場
【其他】印度、東南亞新生代穩定聚焦
綜觀市場消長,掌握投資風向!藏家必備的最佳拍賣市場指南!
何謂漫畫?讓您一覽日本、美國、歐州國際三大漫畫潮流
本圖錄收錄參與展覽之漫畫藝術家作品與相關文章,藝術家有尼古拉.德魁西、馬克安瑞.馬修、艾瑞克.利倍舉、伯納.伊斯列、荒木飛呂彥、克里斯.杜利安、大衛.普多姆、艾提安.達文多、恩奇.畢拉、菲立浦.度比&方陸惠、谷口治郎、常勝、61chi、小莊、簡嘉誠、TK章世炘、阿推、麥仁杰等19位。
聚焦當代藝術市場新浪潮!
現代與當代藝術精品拍賣實錄、華人亞洲區排行完整呈現!
◆吳冠中《周莊》刷新中國油畫拍賣紀錄
◆日、韓躍身國際舞台持續發光;印度、東南亞展望新生代穩定聚焦,2016年是否再創投資新紀元?
趙無極連年制霸、蘇軾《木石圖》躍居古書畫龍頭、乾隆御製琺瑯彩碗竄升億元關……,回顧2018年拍賣,熱潮雖較往年稍降,整體表現依然亮眼,「拍賣大典」一舉囊括重點拍品,幫助藏家輕鬆掌握下一波趨勢脈絡。
從日常到創作,漢寶德漫談鄉土與藝術。
本書共分四大卷,從「鄉土藝術家」、「鄉土藝術」、「鄉土建築」,到「老街」,各卷又有名詞義釋與時事探討的詳正論述,諸如鄉土與民間,本土與外來,手工藝與古董等等,倆倆參照又類比影響的相似卻又不一樣,通通都在漢寶德根深淺出的說明比喻裡,談出另一種或更多的可能。